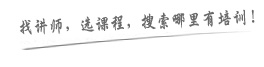稻盛和夫的管理與眾不同,如果不是他創立過兩家五百強公司,如果不是他取得的經營實效,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這樣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能夠成為經營公司的大家。尤其是稻盛和夫自己,本來只是個技術人才,沉迷在新型陶瓷的研發中,在創業之初根本不懂經營與管理,看不懂會計報表,不會進行商業談判,不了解組織原理和領導理論,不懂得如何激勵與控制,沒有營銷技能。這樣的人開公司,多數人會有疑問的。不要以為技術高手開公司就能成功,那種靠某個發明的聰明人辦企業栽倒的人太多了,喬布斯和蓋茨是罕見的低概率案例,常態并不如此。所以,人們對稻盛的成功,往往看作奇跡,然而奇跡確實出現了。
實際上,類似的奇跡,在宗教界早就出現過。公元529年,修道士本尼狄克在意大利中部的蒙特卡西諾建立了一個實驗性的修道士團體。他倡導苦修,反對修士的奢華安逸,出于宗教的虔誠,力圖使修道院具有規范的秩序、組織和紀律,為此制定出《圣本篤規程》(The Rule of St Benedict),共73項條款,規定了修道士的目標、職責、工作和生活規則。如修士不可婚娶、不可有私財、一切服從長上的“發三愿”,祈禱與工作并行,游手好閑為罪惡等規范,就是由他確立的。后來,這一規程在確立天主教的行為規范、保障修道院經營活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為中世紀的修道院是歐洲*的經濟實體,所以西方學者稱本尼狄克為“上帝的企業家”,并把遵循圣本篤規程的修道院看作宗教性公司。11世紀成立的西多會(Cistercian),恪守本篤會規矩,以西多修道院作為“創立者會所”向外擴展,到各地建立“女兒會所”,所有女兒會所保證遵守統一的《慈善機構典章制度》,每個女兒會所建立獨立經營性的莊園,正是由于西多會盡善盡美的追求,才形成了世界聞名的葡萄酒釀造產業,從11到16世紀,它成為繼本篤會后歐洲*的經濟組織。有些專家認為,近代的子公司制就是由此發源的。如果做個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相對于中世紀的修道院而言,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學和經營哲學,就像天主教的《圣經》,而阿米巴同西多會的女兒會所類似,會計七原則和經營方法同《圣本篤規程》與《慈善機構典章制度》相仿。他們的根基,都建立在宗教信仰、人性發現和善行追求之上。
當然,管理思想的探究,不能簡單地比附,而要力求把握實質。本篤會、西多會、稻盛,他們的成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宗教信仰的熱誠,以及同這種信仰相伴隨的苦修。看看稻盛所受過的磨煉,所經歷的坎坷,再看看他在工作中那種近乎自虐的做法,那種對完美無缺的追求,就能明白他為什么成功了。我們常人哪怕十分堅韌,也難以做到完美,往往會接受現實的缺憾。因為我們的理性會不斷警告自己,世界上沒有完美。而稻盛的行為,在很多正常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在一些聰明人看來是“犯傻”的,在心口不一的人看來簡直是“瘋魔”的。所以,如果沒有稻盛式的信仰和追求,那最好不要模仿他。否則,難免東施效顰。即便有稻盛式的信仰和追求,如果你是理性至上者,那也學不了他。稻盛的成功是一種信仰至上的成功,與強調理性的管理案例不一樣。
但是,正因為稻盛的特殊性,所以,他對管理學具有特殊意義。從管理學誕生以來,基本上是理性至上的,這也難怪,沒有理性就沒有科學。然而,管理學對理性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理性之外的東西。盡管隨著社會學和心理學向管理學的滲透,人們也開始關注非理性,但頂多是把非理性因素作為理性的陪襯。而稻盛明確了一點:經營不是不要理性,但理性從屬于信仰。在馬克斯?韋伯那里,是新教信仰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而在稻盛和夫這里,是經營理性從屬于人的信仰。稻盛的這種信仰,不僅來自于佛教,而且來自于生活。這就是他反復強調的“作為人,何為正確”的追問。這種來自生活的信仰,正如中國那些鄉間不識字的老人所說的“頭頂三尺有神明”是一個道理。所以,稻盛要告訴人們的,是在至高無上的理性之上,還有更加至高無上的良心。由于稻盛的入世,所以,他的觀點,與中國王陽明的心學更為接近。對管理思想的研究,稻盛提供了一個探討科學與宗教在管理中的關系問題的絕好范例。
在管理實踐層面,稻盛能給人們提供新的思考。他所創造的阿米巴管理,本質上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自治、分權、參與(合作)。但這三個詞用來形容阿米巴都有局限。阿米巴具有自組織的某些特色,但又不完全是自組織,如果單一強調自治,就會走向個人主義。而阿米巴的自治不是個人自治,其自治單元到阿米巴就不能再分割,而且其自治必須與公司整體高度耦合。稻盛的阿米巴經營,同威廉·大內所說的氏族式社會組織相像。然而,氏族這一詞匯有可能引起中國人的誤解,因為日本的氏族同中國的氏族是不一樣的(日本直到近代之前,只有貴族和武士有姓氏,普通民眾沒有姓氏,僅此一點,就可以反映出日本氏族與中國的不同)。阿米巴同歐美分權經營的事業部制也有差別,各事業部以產品和地區為經營邊界,要保證完整的生產流程,并未把市場機制引入生產流程內部,而且并不保證員工的參與。至于更加古老和更加廣泛的承包制,同阿米巴差別更大。所以,阿米巴經營具有自己的獨特性。管理實踐中可以領會和參照阿米巴經營的精神,如果僅僅是形式上的模仿,不過是給已經用濫的目標管理、績效考核換一個名詞而已。稻盛和夫的會計原則和經營方法,也值得管理實踐者深思,沒有任何會計基礎,反而能夠抓住管理會計的本質;用常識管理,但又不囿于常識;有執著的追求,又能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這些是稻盛和夫之長。作為企業家,需要考慮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具有稻盛的堅韌、善良、悟性,如果有稻盛那樣堅強的意志和追求,如果有稻盛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那么,不論是不是采用稻盛的具體方法,都可能取得成功。而如果這些都不具備,那么,即便把稻盛的方法都照搬過來,只會產生橘枳之變。稻盛真正告訴經營者的是,管理要靠自己,誰的問題就由誰解決。許多學習管理知識和技能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個偏差,就是看能不能從別人那里找到解決自己問題的方法。稻盛和夫告訴你,別人只能給你啟示,路要自己走。尤其對那些試圖在各種管理學說中找到捷徑的人來說,所有捷徑,走到頭就會發現那是彎路,存有機心,是失敗的先兆。
稻盛和夫的成功,對管理教育也是一個警示(喬布斯是另一種類型的警示)。既然沒學過管理也能從事經營,那為什么還要學習?稻盛也好,喬布斯也好,還有相當多的成功企業家,例如臺塑的王永慶,都沒學過管理。而那些商學院出來的并不見得就有經營優勢。這也是MBA教育深受詬病的地方,已經遭到了從厄威克到明茨伯格的不斷批判。實際上,稻盛不是沒有學習管理,而是在實踐中學,向他的團隊中那些具有專業知識的所有人學,這種學習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學習的主動性和自發性。*說過,任何學習,到頭來都是自學。所以,管理教育靠外在的灌輸無濟于事。教育者的作用,不是替代受教育者走路,而是給受教育者提供路標和方向信息。正如稻盛信仰的禪宗,不立文字,萬法盡在自心。教在佛祖,悟在自己。跟風式的學習,只是邯鄲學步。稻盛和夫能夠表達出來的東西,在那些缺乏內在學習動力的人看來,不過是一些“老掉牙的老生常談”,“人人皆知的普通說教”,殊不知即便是佛祖所言,在不信佛者那里也不過是過耳即忘的“如是我聞”。還有一些人推崇稻盛和夫,是覺得稻盛和夫的東西通俗好學,同中國的語境相近,然而能否像稻盛那樣做,恐怕十分困難;學了又做不到,那就徹底違背了稻盛和夫的本意。管理教育如何能夠滿足管理實踐者的需要,還需要認真探討。
從社會環境來說,馬克斯·韋伯告訴我們,真正的企業家要有“天職”意識,而沒有宗教文化的環境,不可能形成天職觀;缺乏信仰,不可能產生神圣感。稻盛和夫則告訴我們,不僅西方如此,東方也如此。所以,稻盛以信仰駕馭理性,以常識引導理性,以理性踐行信仰,以理性修正常識,這是他對管理學的*貢獻。
文/劉文瑞:西北大學公(gong)共管理學院教授(shou)
轉載://citymember.cn/zixun_detail/29127.html